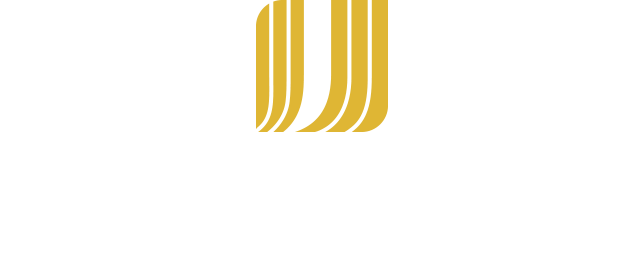由江西文演集团与北京舞蹈学院共同出品的舞剧《天工开物》,其创作源于同名古籍。自2024年首演以来,该剧已在国内20多个城市巡演6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过97%,观众累计7万余人次。这部承载着江西文化底蕴与中华传统智慧的艺术作品,在全国开启了一段独特的艺术旅程,掀起一阵“天工热潮”。2025年连续演出排期超100场,其中海外巡演7场。今年6月该剧登陆纽约联合国总部,亮相“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表演并获好评,剧组海外演出载誉归来后,又二度进京倾情献艺。
分镜特写化舞图,应天星斗落氍毹。笛引春烟浮黛瓦,箫追秋色入霜炉。场刊的抢眼位置标注电影导演陆川首次尝试舞剧创作,他身兼总导演、编剧和总制片人,在导演自述中言道:“我很荣幸能够踏上江西这片古老的土地,邂逅了《天工开物》这本著作及其作者宋应星。这次相遇,让我感触良深。宋应星身上承载着科学的精神,为这个国家民族的科技传承,付出长期而孤寂的努力,在明朝国破家亡之际,靠一己之力把中华民族先进的科学技术汇聚在一本书里。他是一个时代的逆行者。我渴望探寻他灵魂深处那股力量,也希望《天工开物》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们,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与追求。”陆川试将电影分镜思维引入舞剧中,用独舞、双人舞及三人舞聚焦人物内心独白,以全景式的群舞调度展示历史风貌。
万物生长,时序轮回。书中“乃粒”“乃服”“冶铸”“锤锻”“膏液”“陶埏”“佳兵”“舟车”等十八个篇章,对明朝中叶以前的科学技术工艺进行完整的考察梳理,记录中国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几千年来的实践技巧。舞剧《天工开物》冲破了传统观演边界,暖场时的舞者化身“雕塑”立于舞台,观众走近顿觉生机;劳动者扛着农具从观众席走向舞台,模糊了现实与表演的区隔,呈现出主创团队的慧心巧思。
好的艺术作品需要用大量的心力和创造力去一点点地开凿、雕琢、重修甚至重塑。交织着苦难与成就感的舞剧《天工开物》是那样迷人,释放出穿越时空的艺术联觉之力。剧中宋应星等人物状态如静水流深般自然铺展,不卑不亢、如松如岳。在创作团队不断地修改巡演中,观众也反复确证《天工开物》所具有的丰沛广阔的开掘空间。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不同艺术形式间的一次共舞,让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布衣飞扬、跃动人心,共同绘制出一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国工艺百科画廊。
舞剧《天工开物》的创作时空观念自由、情节浓缩、类型叙事成熟。它能抵达观众情感深处,实现技术与情绪的平衡,给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该剧的舞美设计参考了相关史料,通过对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资料的研究,总结出“大、巧、简”的美学特征,原书《天工开物》中的123幅白描绣像插图,是典型的明代版画特点,也成为贯穿全剧的美学元素。在灯光设计上,根据剧情需要,或交叠或分离,呈现出灵动写意的舞台画面;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剧情的展现,增强视觉效果,并且结合灯光变幻延展舞台空间,勾勒出“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的奇幻之美。在装造上则参照明代中晚期的服饰特点,在遵从史实的基础上,设计出官员、工匠、农夫等舞剧人物造型。全剧的音乐以丝弦乐器为主,辅以笙箫钟等管乐和打击乐,还采集了劳作的原始声响作为背景音使用,如打铁、抽拉风箱、稻浪、浇筑、耕作、劳动号子等素材运用。
全剧在叙事上重情,强调戏剧冲突与人物内心的变化。画面上讲究情景交融,营造一种“情与景偕”的效果。借助中国传统艺术的游观、散点透视方式,多采用“横移镜头”的理念手段,将人物与景物统摄于舞台,创造出流动的诗意感。作品整体的审美旨趣,可用“随类赋彩”“气韵生动”来概括,即追求一种炽烈又质朴、丰沛又节制之美。但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美只是一个起点,美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它可以是形式上的和谐,也可以是感官上的愉悦。我以为,艺术创作的核心使命不仅仅是美的表达,而是通过对艺术表现形式的不断探索,完成对不同题材意义的探讨;艺术创作也不仅仅是创造一种形式或感性的享受,更彰显创作者的思想表达。因此,舞剧《天工开物》不只有表面上的美感,更是与古人对话——不断追寻科技与艺术的本质、人类情感的深度,以及对古代文明的充分认知对当下的意义。
舞剧《天工开物》是江西文演集团推出“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的首部作品。它就像一颗深埋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种子,破土绽放出兼具传统精神与现代美学的艺术之花,以此向300多年前的先辈致意,并在传统与现代的激流中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剧中描绘了宋应星等有识之士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记录着民族科技工艺的可能与局限,以此试图还原我们古代文明的五彩斑斓。舞者用身体呈现科技、艺术的图景,解读舞剧艺术在叙事状物与雅俗共赏之间的张力。作品所呈现的若干繁复时空,错落之间存在内在秩序,成为一场有关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日常复现。超越时空的风格化元素被杂糅在一起,吸引观众们的目光。
导演陆川有意识地使电影意图转化为舞台剧的创作思维。这种转化,表面上看是客观的、写实的,实质上却是主观的。舞者“抽帧式”的肢体表演在钝感化造型与灵活行动之间达成一种动静平衡,这种独特的舞台美学风格是陆川借助舞者的身体而构建完成的。他让身体、结构、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视差转换,形成间离的视觉效果。他以一种带有“生活诗学”的方式展开叙事,让观众在感知节奏中体会变化。舞剧四幕场次的自然过渡,仿佛是一次缓慢展开的视觉旅行。从视觉呈现、空间叙事到与观众互动,体现出极高的剧场系统协调度。陆川关注微观层面的相互联结,体现了从剧场实践出发的创新思维和观念反思,展现出舞台剧别样的表演方式。
第三幕《著书》,随着木版雕刻的声音响起,声声扣人心弦。宋应星的精神焕发,白描秀像的雕版插画逐渐栩栩如生。他倾尽全力,挥洒最后一丝墨水,终于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语:“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一张张书页在工匠们的手中传递,经过精心的印制,最终汇聚成一部辉煌的天工开物之作。此时,在“书成”营造的视觉景观里,导演借助舞台“容器”,超现实地将自己对宋应星及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感受呈现给观众,肃穆而凝重。
第四幕《山河》,乱世之中,铁蹄践踏,战乱席卷大地。工匠们曾享有的那份安居乐业已不复存在。宋应星怀揣《天工开物》,如一位孤独的战士般坚定地守护着,用身体捍卫着这个天工开物的世界,那是他心心念念的文明版图。然而,在战火的无情肆虐下,他内心的希望与信仰在乱世中飘摇。书已成,可兄长、挚友已逝,国没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宋应星和那本书。漫天纸张飘零,犹如纷飞的花瓣在风中轻舞,簌簌之声传遍四方。灯盏忽明忽暗,仿佛是纷乱之世中摇摇欲坠的星辰。宋应星身影忙碌,伏案疾书,翻书声与合书声此起彼伏激荡人心。这场“如雪片般飞舞”的桥段让我记忆犹新,它更像是参与叙事的“视觉角色”,织与写、手与心、工艺与舞动在此交会,不动声色地体现了对“传统媒介转译”的探索:不是复刻传统,而是在精神上回望它,在形式上更新它。
整体看来,该剧风格恢宏有力,偏重烘托气氛而略失于细腻表达,也许是因应当代舞台艺术视觉震撼力强所致。既然是舞剧,便不可只注重“舞”之技巧编排,而轻“剧”之连贯周延。舞剧《天工开物》,好就好在它通过舞剧塑造一个历经六次科考落榜,却痴迷于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有血有肉的宋应星的人物形象。他本想以自己的笔墨拯救危亡的国家,却无法阻拦山河破碎,兄长、挚友以身殉国的遭遇。宋应星进而静心执着于做一件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更有意义的大事,著就《天工开物》,记录、传播中国科学技术。今天,这样的他被立于舞台之上,值得称颂。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作者:金浩)